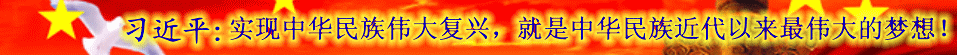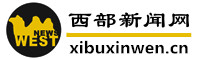一、觅汀兄
昨晚睡得早,今天也起得早。早上起来,第一个意识竟然是想起觅汀兄。
我们写文章,常常忽视自己身边的人,写文章就像画画,大写意好画,工笔难描。于是就常常对自己熟悉的人无法动笔。因为了解的太多,反倒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觅汀兄与我交往几近三十年,到今年,我一共在这个世界活动了五十年,他对我的影响,就占了我生命的大半。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陕西师大读中文系,觅汀兄在我们班插班。那时候,我们这些正规考上大学的,都是一条线,从小学一路考上来,除了读书,别的事情都很懵懂,倒是那些插班的,都是从各单位来的,年龄稍长,都颇有些经历和胆量,敢对着老师顶嘴,敢对着女生丢眼神,搞得我们心中既吃惊又嫉妒,常常在心底骂一声“流氓”。
觅汀兄就是我们班插班的之一,他那时候很有风采,长发披肩,又有几分卷曲,从后边看宽肩细腰,有几分齐秦的样子,那时候他常和一个留着马克思胡子的大个子在一起,二人常常抱个厚厚的大坐垫,上课的时候一起来,下课的时候一起走,很少和我们说话搭腔。我那时候常想,这些怂人的尻子生得不知道有多金贵,整天抱个垫子垫着。插班的都不和我们一起住,他们住在学生宿舍楼的地下室里,所以,上课和吃饭的时候,他们一阵风钻上来,下课了,都消失不见了,形同鬼魅一般。
觅汀兄背影很像齐秦,但是五官却与齐秦无关。那时候我仔细看过,他双眼似牛眸,大而露出楚楚动情的样子,鼻子扁平,有点兔鼻的意思,嘴大而阔,牙小儿齐,神态率真,是很会招惹女生的那种。 他的长相,是南方山地人的典型。
有一天中午,正是午休的时候,觅汀兄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邪火,他从地下室里冒上来,手里捏了一片树叶,在我们宿舍楼道里四处吹,吹了一段段南方小曲,搞得我好奇万分,竟然放下了学生会主席的架子,跟在觅汀兄身后,一路看热闹,串走了好几个宿舍,那片树叶在他手中,竟变得神奇得很,个个曲子都吹得合辙而圆润。我们一伙同学都围了听。觅汀兄吹的时候,他的两只含情楚楚的牛眸,还盯着你看,搞得人心里瘙痒难耐。那一次,他竟然用一片树叶,把我领到了他住的地下室里。此后,我常想,南方山中人有赶尸的本领,其实他们驱赶着的不是尸体,而是人的灵魂。觅汀兄就有这样的本事,他用一片树叶,一路吹奏着,把我的灵魂牵引走了。
觅汀兄是南方人,他的家在乌蒙大山之中,所以他歌唱得好,并且会吹树叶。我在树叶悠长而入耳的声乐中,跟他下到地下室。地下室是50年代的人防工程,要下许多楼梯,才拐进一个大铁门,只见那是一个漆黑阴暗的所在,四周是水泥坚壁,冰冷异常。觅汀兄住的地下室,有三五十个平方,分成左右两间,右间不小,住了许多插班的,左间不大,有三五个平方,角上放了一个巨大的抽风机。觅汀兄的床就放在抽风机的旁边。床上铺盖是军用的绿色,叠得整齐有致。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次我的地下室之行,竟是我生命的一个巨大转折。
我跟觅汀兄聊起天来,没想到竟是非常的投缘,我知道了,觅汀兄从贫瘠的乌蒙大山中走出来,16岁当兵,20岁娶妻,此后收获一子一女。他那孩子般率真的脸上,是永远无法破译出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当铁道兵,在青藏高原上打隧道,喂猪,想老婆,后来跟随十万铁道兵一起,被邓小平一个手势复员成了铁路工人。
觅汀兄是有心机的。他对艺术很灵性,再加上他心底柔弱,诗情画意常在心中。但是他只是一个高中上了一半的文化,就常常思谋着再上大学进修。他兵改工后来到咸阳,被派去当理发员,理发室里常有领导走动,觅汀兄决定了,改变命运从理发刀上开始。一天夜里,有高层领导来理发,觅汀兄就大展才艺,把领导那大方头理得威武异常,领导平常佝偻着的身子也跟着挺直了,就一面照着镜子,一面一幅关心下属的表情,问觅汀兄有什么困难。觅汀兄故作为难,声音压得低低地,说出上大学的心愿。领导豪放地表态了,说,你这小鬼,爱上学是好事情嘛。于是,觅汀兄被送到了陕西师大的地下室里,成了一个插班的。
我常常对觅汀兄的心机唏嘘不已,更对他的才情钦慕不堪。觅汀兄唱歌、写词、摄影都在道上。于是,地下室成了我在大学后两年的寄居之所,我将我自己宿舍的被子叠整齐,去把觅汀兄的被子拉乱,不管白昼与暗夜,都躺在他的床上,而他就只好端坐在凳子上,我们谈话的水流可以奔涌到时间和空间的任何一个方位。我不得不承认,在两个方面,觅汀兄是我的导师,一个是对于女人,另一个是他让我知道了,我是一个有艺术才情的人。
前几天我无意间翻出影集,我发现从我的大学时代开始,一直到近期,我的大多数照片中,要么有觅汀兄的身影在其中,要么是他拍摄的。这其中也有不少女孩的照片,她们大多是觅汀兄的粉丝,觅汀兄的歌声、摄影、诗歌的才华,特别是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都是女孩们深深地陷阱。只不过,因为他早已经是为人夫为人父的人,才使许多女人长叹一声而离去了。
我们离开大学的时候,各自惶惶不安。觅汀兄被一辆车拉回了咸阳,我分配到西安西郊的一个单位,相距不算太远,也就常有往来。此后,我写的许多书中都有他的文章。他也在我的生命之树上加深刻痕。觅汀兄刚回单位上班,被分去开电梯,就经常腰间挂一大串钥匙,把电梯开得上下跑。那一年我结婚,就电话告知了觅汀兄,觅汀兄因了要开电梯,白天没有时间来,就半夜来了。那是春节刚过,三九天气,严寒如铁,兄长来参加婚礼,不能怠慢了,我就安排觅汀兄与我住在新婚的床上,我的新娘则独宿在室外的沙发上。此后,我想,新婚之夜与兄长住而远离新娘的,这世界上可能就我一个人吧。
觅汀兄后来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再次动用心机。他不想开电梯,因为那东西与艺术无关。觅汀兄观察发现,每天早晨,领导都是要到单位外跑步的,而且跑得不近。觅汀兄仔细研究了领导跑步的轨迹,并画出许多草图来。他就每天早起,提前跑到领导要拐弯的地方等待,领导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手下中竟然有如此才华的小青年,就一句话把他调到宣传部了。觅汀兄到了宣传部,就如老鼠进洞,小鱼入水,文章写得满天飞,照片发得报报有。领导拍着报纸大声说,看我的眼力不错吧?看看!那一年,觅汀兄单位要写企业歌,那歌词就是觅汀兄写的,一直传唱至今。
觅汀兄发展的路子是新闻,特长是摄影,他拍摄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蒙古大草原都美轮美奂,常令人神往不已。他已经成为一代摄影大家了。我和觅汀兄的交往深刻而漫长,此刻我要住笔了,因为他最近常常心悸,胃也有些不适。我不敢把一个好友的文章记述到现在,要留些,在老来回忆并记述。
我盼望着我们能相随到久远。
我与觅汀兄(右)
二、陈抱思(booes shen)
我和外国人打交道,开始于上个世界80年代,那时候,我在师大上学,师大有许多外国留学生和外教,外国人正式出现在我面前,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那时候,有一个叫陈抱思的荷兰人,在我们班上插班留学,陈抱思那时二十五六岁,比我们班的同学大四五岁。陈抱思是典型的西欧人,个高,眼睛碧蓝,皮肤白嫩得能看见像细蚯蚓一样的血管,头发金黄卷曲,但乱糟糟的像一团麻丝。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正上古代文学,陈抱思被代课老师领进教室,老师介绍说,这是新来的留学生陈抱思,我们抬起头,只见一个瘦得像鸦片鬼一样的年轻洋鬼子站在讲台上,他穿一件中国军人常穿的军大衣,由于衣服宽大,他的身体就像一根竹竿,在那里挑着衣服。他的脸通红的,可能是因了天冷,也可能是因为害羞,反正他的脸那天红的像关中产的辣椒,红得可以!
老师介绍完,陈抱思吭哧半天说,我叫陈抱思,来自荷兰,大家多帮助。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见荷兰人发出的声音,而且还是中文,也可以说是怪腔怪调的普通话。虽然荷兰人在17-18世纪曾经称霸世界一时,虽然这个海上强盗国家曾经多次蹂躏过我们国家,但是,我第一次听见荷兰人说话,就从陈抱思开始。
陈抱思说完,按照老师的指定,就一蹦一蹦走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坐下了,而我也坐在最后一排,最后一排坐了两个人,那就是陈抱思和我。
我斜眼看了陈抱思一眼,陈抱思满脸谦卑的冲我笑笑,就坐下来,我突然惊奇的发现,陈抱思高大而弯曲的鼻头上,挂了一道闪闪发亮的清鼻涕,接着陈抱思一连打了几个喷嚏,惊动得所有同学都回过头来看。陈抱思更加羞涩,将头伏在桌子上,拿出纸来擦鼻。我第一次看见陈抱思,到底是惊奇?还是鄙视?还是其他什么别的感觉?此刻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陈抱思以后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直到30年后的今天。
那天下课,老师走到我身边,对我说,我是班长,以后要带好陈抱思。我说好呀!没吗哒呀!这是一句陕西土话,意思是说没问题。
既然答应了老师,我就得带好这个洋鬼子,但是,令我讨厌的是,陈抱思的身高可能超过两米。我对他说话,总得仰着头。中午,我带着陈抱思到食堂吃饭,这个头上顶着乱麻丝的瘦高个,在人群中总能找得到。我说,吃面吧。他说,吃火腿。我说,吃米饭,他说,吃火腿。我说,你吃你的,我吃我的。陈抱思说,中国人步调要一致,这是《人民日报》上说的。我说你不是中国人,没必要一致,再说我也不吃火腿,你也不吃哨子面,怎么一致?陈抱思满脸无辜,有些拿不定主意,这时,我们班一个长得很漂亮的西安姑娘走过来,我终于找到救兵,就喊她过来帮忙,带陈抱思去吃火腿,她高兴地带着他去了。八年之后,她成了他的第二任老婆,一切都是缘分呀!这狗日的陈抱思。
陈抱思说话很难听,在欧洲,荷兰人说话难听,那是举世公认的。他们说话的声音不是从口腔中发出来的,而是从后脑勺发出来的。英语中有一句成语,翻译成汉语就是“比荷兰还荷兰”。说的就是荷兰人说话难听。
在大学,每一个留学生都要和一个本国学生结对子,叫做“陪读,”为的是双方加强交流,尽快学习彼此的语言。陈抱思是我的“陪读”,我也是陈抱思的“陪读”。陈抱思会说许多中国话,虽然发音不准,虽然声音古怪,但他毕竟懂些中国话,但我却对荷兰话一窍不通,我们只能简单交流,再配合手势,再加几句简单的英语。
老师说,教“陪读”对象学中文,是我们的责任,我也觉得责任重大,教不好牵扯国家形象,于是,我决定认真教陈抱思学中文。我决定从骂人教起,让他掌握陕西话的精髓,因为陕西人教孩子学说话,都是从骂人开始。
我告诉他:“有人欺负你,你就骂他‘妈pi’”。
陈抱思果然是个天才,他没有演练几次,就学会了。
一次,我和陈抱思到小寨街上闲逛,陈抱思用他那穿着46码大鞋子的脚踩了一个中年女人的脚,那女人像被蝎子蛰了一样大叫一声,接着就开始发出一连串的咒骂之声,当时,那女人都说了些什么,此刻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其大意我是记得的。她说,你是个什么东西敢踩我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娘是什么人不要说你是外国人外国人有什么了不起踩了老娘的脚你就得赔赔少了还不行老娘饶不了你——。我当时感到有些惊慌,因为我知道,西安是有许多闲人泼妇的,他们专门在街上滋事,目的在于讹钱,我想拉陈抱思快走,不料陈抱思却像一只鸵鸟一般高高地站在那里,而且脸上充满笑容。在那女人骂人的间歇处,陈抱思像插入标点符号一般不失时机的说一声“妈pi”。而且发音极准确,让所有人都听得真切。
那女人被陈抱思激怒了,她开始了又一阵疯狂咒骂,而且嘴角的白沫已经开始乱飞,此时,再看陈抱思,依然笑容满面,依然神情自若,依然用“妈pi”之盾,阻挡那女人射来的上万枝咒骂之箭。此时我才知道,荷兰鬼永远是荷兰鬼,他们不愧是海盗出身的国家呀,他怎么会惧怕长安街头的一个泼妇呢!
此后,陈抱思在我的调教下,汉语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都是陕西土话,他心情不好会说“募乱很”,讨厌谁会说“哈怂”,对什么不满会说“锤子”,斥责别人会说“少骚情”,有时候还会说“日八歘(chua)”。2009年春,我到荷兰,见到分别近30年的陈抱思,在阿姆斯特丹机场,陈抱思嫌收费处的女检票员动作慢了,就大喊一声:“挨球的”。惊得周围的各国旅客一起观望,只听那女检票员说“think you”。陈抱思笑了,说,老师,咋样?我感到由衷的自豪,甚至有几分激动,看来我们民族文化特别是陕西文化是战无不胜的。
陈抱思也有走麦城的时候,他学了半年汉字,一次和我上街,就耸耸肩不以为然地说,中国人什么都行,但是没有必要都写在大街上。我觉得奇怪,就问他why?他说,你看“中国农业很行”“中国人民很行”“中国交通很行”“中国工商很行”,都很行,我仔细一想,明白了,原来那些不是“很行”,而是“银行”,这狗日的陈抱思分不清“很”字和“银”字。
陈抱思也有深沉的时候,他曾经很认真地告诉我,《人民日报》上说要步调一致,中国这么多人,怎么可能一致呢?我说,那是指思想上。他说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不应该一致。我顿时无语,我知道,这句话暗示了一种变革,一种我所期盼的变革!我告诉他,孔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孙子的思想是不一致的,但是他们也是中国的思想。陈抱思从此开始关注这些古代先贤。他现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汉语,还是什么教授,他的古汉语知识大多来自于我,而不是我们中文系的那些教授们。
1984年,陈抱思从西安去台湾,他走的时候,在他的所有书籍上都留下了我老家的门牌号码,那时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没有电子邮件,只有信件和邮差。他说他怕从此和我断了联系。但是,从此我们确实断了联系,此后20多年里再没有这个荷兰鬼子的任何消息。我有时也难免叹息,这些洋人是无情无义的动物,他们只比猴子进化了些,属于“沐猴戴冠”,不管他们有求你时是多么恳切,但是一旦人走茶就凉了。我从此也就忘记了这个曾在我生命中留下许多回忆的人。2009年春,我被德国人敲诈,不得不去荷兰和德国人周旋时,却意外地和陈抱思见面了。
陈抱思留下我老家的门牌号,我同时也留下了他家的,我到达荷兰,在阿姆斯特丹,我对前来接我的朋友说,我的一个同学住在阿姆斯特丹,并说出了他家的门牌号,那天我觉得特别奇怪,他家的门牌号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平时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其实,在心底里我是惦记着这个朋友的。接我的朋友说,此刻我们就走在你说的那条街上,你看,你说的号码就在我们汽车旁,要不要下车找一下?我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下了汽车,径直走过去,只见一个胖老妇提着水桶走过来,她看见我,打量一下,叫了一声“shi”。我大吃一惊,在陌生的地方,怎么会有人呼唤我呢?那老妇确实是对着我呼喊“shi”。我狐疑着走过去,那老妇笑成一朵白色的菊花,此刻,她的身后又站了一个人,那正是陈抱思。陈抱思扑过来抱住我,大喊“老师,石。”又说了许多陕西粗话,我都不好意思写出来,反正是骂我的,我都后悔当时教他了。他拉着我进了他家的楼房,并对着楼上大喊:“静静,快来,石来了。”此时楼梯上下来一个胖女人,仔细看半天,才辨认出,正是当年我叫来陪陈抱思吃火腿的西安漂亮女同学,我的神呀!已经胖成马了!
陈抱思一家把我接进客厅,在客厅最醒目的地方,我看见一张巨幅照片,那正是我和陈抱思的合影,我们像两个傻pi一样,直直地站在西安钟楼底下。
陈抱思
三、泽辉兄弟
泽辉兄弟是青海人,姓俞。他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比我小,所以我称他为泽辉兄弟。
初识泽辉兄弟,是因为一次画展。2012年6月,我组织关爱母亲河书法绘画作品展。老哥朱正告诉我,有一个年轻画家,要为画展创作一幅画。我听了有些激动,因为这个年代,任何东西都是商品,不管是女人的身体还是男人的灵魂,都明码标价了。我们在西安书院门,看见那些站成一排,像农夫买菜一样,把艺术二十三十往外卖的所谓艺术家。我在组织书画展的时候,常常会遇见讨价还价的书画家,一幅猥琐不堪的样子,把手捏成一个“七”字型,问你要回报。而这个画家竟然不动声色要为画展创作一幅画,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我当即要了画家的电话,直接打过去,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很男人的声音。我说,我要去看你。那声音也很激动,说,请来吧。
于是,我开车到了西安二环北路的边上,在约定的地点,一个留着长发的壮汉在路边站着,我们相视一眼,我便知道,他必定就是画家俞泽辉了。这不是因为我熟读易经,也不是因为我会相面,而是因为他的气势。那天,俞泽辉站在那里,健硕的身材挺立着,长发在风中飘摆,一双细目充满泽光,满脸是谦和从容的笑意。我知道,只有脸上有这种谦和之色的人,才胸中有爱,才能做出奉献的义举。我们四手相握,从此,他成了我的泽辉兄弟。
泽辉兄弟拉着我的手,我们一同进了他的房间。他的房间不大,只能算蜗居,在只有不到十个平方的客厅里,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泽辉兄弟刚刚画完的一幅创作画,那画画的是一个僧人,在拜佛朝圣的旅途上,一手转着经筒,一手抚摸着大地,那僧人的脸上,正是泽辉兄弟那种表情,谦和而从容。我的神呀!泽辉兄弟!
仓央嘉措在一首诗中写道:“因为心中热烈的爱慕,问伊是否愿作我的亲密的伴侣?伊说:若非死别,决不生离。”看着泽辉兄弟的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几句诗,我明白了,泽辉兄弟寄居西安,西安不是他心灵的归所,而是他求佛朝圣旅途中的一站。我再次回头看他,我不由得热泪盈眶。他已经不是我刚刚初识的泽辉兄弟了,他仿佛就是我前生转山路上一同长跪不起的旅伴。兄弟,我们前世是在哪里分手的?今天却在这里相见了?
人有时候就这么奇怪,有人朝夕相处,却终生如同陌路,有人四目相望,便能心灵相通。我和泽辉兄弟就是四目相望便心灵相通的人,他将他的画作一一展示给我看,那些画不是画匠的技巧雕琢,而是心灵飞升过程留下的点点足痕,泽辉兄弟的心灵是属于佛的。
泽辉兄弟为母亲河画展创作的是一幅长卷,因了画卷太长,他客厅的地方太小,他只能把宣纸一头钉在墙上,大部分卷起来,边展开边画。此时,我只能看到画的开头部分,那是青藏高原,崇山巍峨,蓝天似靛,一位阅历沧桑而心灵圣洁的母亲坐在那里,温顺可爱的羊群围在她的四周。我知道了,这就是黄河母亲。我的心灵再一次颤抖。我的神呀!
此后,泽辉兄弟与我常常相见,我喜欢听他用嘹亮质朴的嗓音唱青海花儿,而他喜欢听我讲的《心经》,我们一起朗诵仓央嘉措的诗:
那一日,
我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
蓦然听见你诵经的真言。
那一月,
我摇动所有的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
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不为觐见,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转山转水转佛塔,
不为修来世,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泽辉兄弟在寺庙
泽辉兄弟与他的巨幅画作《一水天来》